2024豆瓣年度作者、年度图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的作者ale(亚历)的个人专栏 ✍️ 每月更新两次
疲劳公告:专栏更新推迟几天
大家好!自从3月10日回中国后,我开始高强度安排书店里的活动,一激动局面有点失控了,从山东到浙江,从江苏到昆明,最近又在成都和重庆,24天内安排了12场分享活动!有些高估了我的身体,到了云南那天......
说破无毒:对世界的好奇心,原来也会耗尽的
2025年2月27日,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自从我和刘水开始旅居的生活过了整整两年。人手一只行李箱装着全部家当,我们一起游走了十个国家,搬了二十几次住宿,连了一百多个w......
离开帕多瓦
1月11日,我们离开意大利了。
我爸发烧了,我妈害怕开高速,所以我们就在客厅告别了,由家里的一个朋友来把我们送到特雷维索机场。
刘水坐后排不停地哭,我坐副驾驶和布布叔叔进......
十年后,三个老同学和一个下午茶
意大利帕多瓦,翁贝酒馆。圣诞假期让大家都顶着低温出来喝一杯,和好友相互祝福。在嘈杂潮湿的环境,我把双肘放在吧台上,声音沙哑地跟芳芳和安东用中文聊天,像个前一天晚上在球场喊疯了的球迷。实际上我只是......
在意大利的温州餐吧,和我爸一起看球
本文应约为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创作,在此为专栏读者的阅读便利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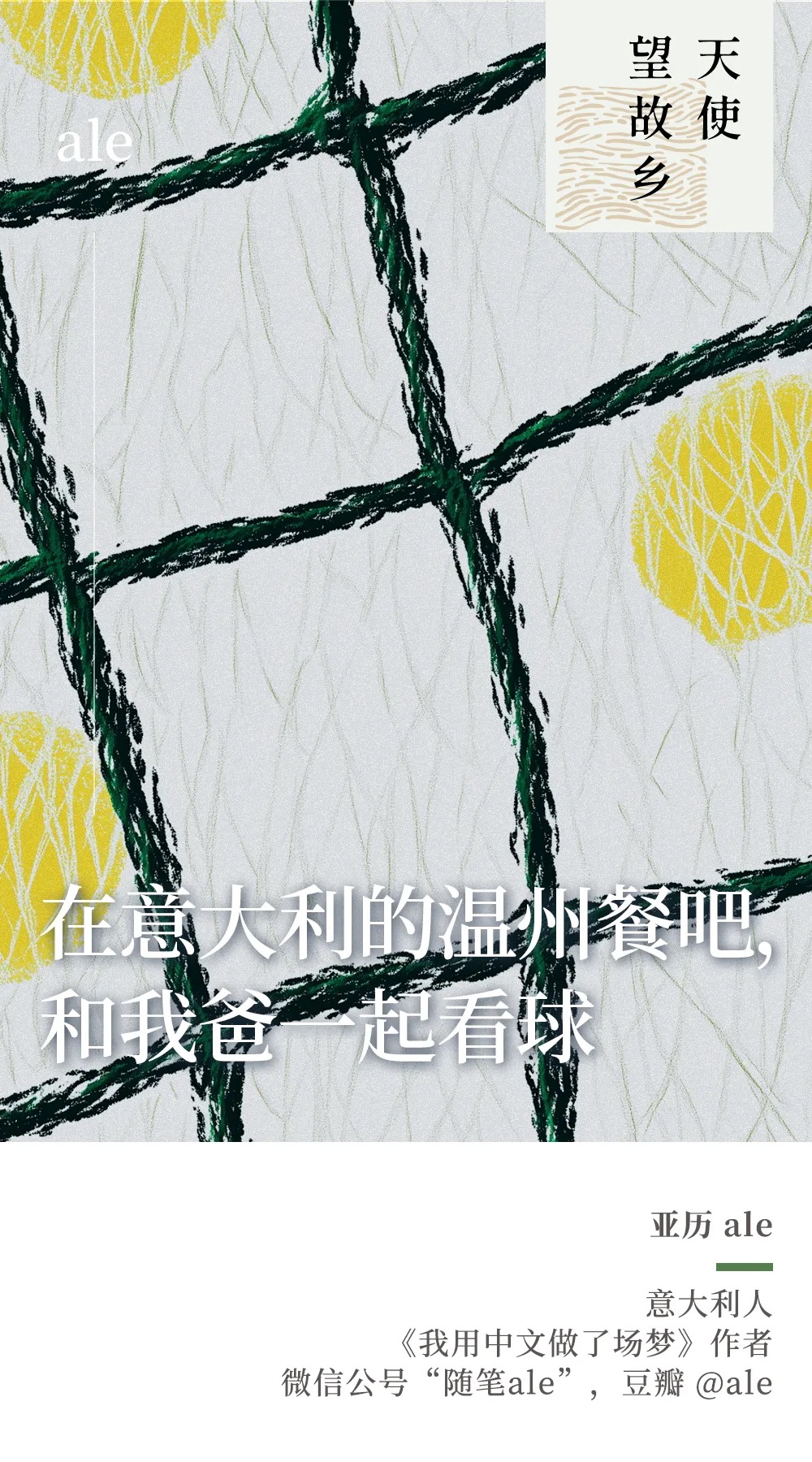
最近,我回了意大利,准备在老家帕多瓦呆到圣诞过后。我算了下,离开家里去上大学到现在有十一年了,在那期间偶尔会回家,但总感觉只是路过而已。而这次,我是真的回来住了一阵子,三个月,一天天地和父母相处,那是足够于习惯彼此的存在的时间。有天早上,我妈走进厨房说过:“看到你在这里感觉很正常,但其实并不正常。”
回到我成年前的家中是充满着错位感、仿佛失真的体验。十多年了,一切都还是一样的——我爸刚睡醒低沉的声音,我妈给人打电话自报姓名的习惯,晚餐时放的欧美六七十年代流行乐。这些日常秩序被维护得程度完美到家里像一座日复一日上演的真人博物馆。我呢,不知道是要演什么。这对于父母是几十年来形成的惯性,对我则是临时的闪回,使我有些难以找到合适的姿态。光从我吃完饭站起来说“谢谢”的行为,我能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有一点像客人一样的感觉。我比较挣扎的表现有时会被欢迎,像当我主动洗厨房里所有的碗;有时会给父母带来不便,例如当我把各种插座拔掉或关掉所有灯的时候。这是我离家以后才学会的环保习惯,现在回来,对爸妈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文化冲击。我妈还认为,最近家里很多灯泡烧坏了是我的错,因为频繁开关“对灯泡不好”。我发现,困在陌生的熟悉感,我唯一仍如鱼得水的活动,是和我爸一起看球赛。
和十来年前的一个区别,是家里没有付费电视了。初中时,我为了这个有些奢侈的消费游说成功了。现在付费电视比当时还贵,加上我不在家住了,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爸选择不再续费了。他开始去一家温州人开的餐吧,和他的老朋友卡罗一起看——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可能还因为一个人在家里看比较孤单,不如到餐吧凑个热闹。在因为什么原因去不了的时候,他会直接找我要球赛的盗版链接,我会给他发那种赌球大哥解说的中文直播。那是我在中国时少数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我爸有交集的瞬间。
我爸和卡罗都是50后,他们是在初中时踢学校的联赛认识的,友谊已经持续六十多年了。在退休之前,卡罗是一个房产中介,下班和周末兼职当足球教练;他的女儿和儿子也都踢球,女儿还踢到了意大利级别最高的全国女足联赛。在卡罗的生活里,足球是很重要的。他对此有很深的认知,还有强烈的观点。不管是看球还是带队,卡罗是坐不住的类型,激动得走来走去,一会儿指挥一会儿骂裁判,一场比赛下来,我估计他消耗的热量比他的球员还多。和我爸那样冷静内向的人,关键词是“passion”的卡罗还是形成鲜明对比的。如果你相信“互补”的定律,那他们是很好的代表。
回想起来还挺神奇。2003年,十岁的我,和这两个成年男人聚在我们家里的地下室,对着电视机共度近乎神圣的时光。在球赛的90分钟里,生活有很不一样的规则。裁判鸣笛比赛开始,现实中的其他问题都不存在了。明天的数学考试还没开始准备,都无所谓——我作为儿子的义务,父亲对我的责任,还有卡罗生活中那些我并不知道的烦恼,全随着我们的社会身份一并淡出了。
我们三个人坐在那儿,一起期待着同一个结果,算是实现了很了不起的状态:我们是平等的,无条件包容和接纳彼此,甚至欢迎其他人加入。对一个球队的爱,让我们形成了虽说转瞬即逝、却极其难得的乌托邦:在这里,无论如何,不会有人说你,也不会有人排斥你。比起球场上的结果本身,还有伴随着的喜怒哀乐,那样的归属感要更加重要。仔细一想,我的内心很少感到过像看球赛时一样安全。这个暂时的家,对我来说,要比每一天的家或比任何朋友更靠谱。没体会过这一点的人,确实只看得到二十二个在球场上蹦跑着的成年人;对此没有什么感觉,也是自然的事情。球赛输了有时候会难过很久,二姐会劝我说,这是一场游戏而已。但显然不是。
对了,我们支持的球队是AC米兰——不管你的老家是哪里,意大利人经常会选择支持一个“强队”,毕竟大家平时关注的是最高级别的“意甲”联赛,而家乡的球队并不一定会出现(最近一次帕多瓦球队进意甲联赛是二十七年前,1997年)。也有人会选择支持家乡的弱队,愿意接受看几十年的三级联赛,并以自己能吃这样的苦的事实为傲。我呢,是因为最单纯的理由选择了AC米兰:上小学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托比亚喜欢。有天课间休息,其他同学来问我喜欢哪个队,我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了AC米兰。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一说了就改不了的事情。
几乎改不了。当时,我还成功把我爸这样平常总是不动声色的人连带一起入坑了。他在成年后的生活主要专注于事业,是家——单位两点一线的人,也逐渐失去了少年看球的乐趣。他身上还有一点原罪,就是小时候喜欢过国际米兰。但经过很多年的“无队论者”的时期,再加上我和卡罗的二次洗礼,他在红黑的大家庭找回了正路。卡罗就没有黑历史——一直都是红黑。
看球赛,也是我第一次见证我爸失去他平时的那副沉着、滴水不漏的样子,包括骂脏话。我们家里的和谐氛围有时靠近那种一家子元气满满地起来吃早餐的饼干广告。我没怎么见过我爸和我妈争吵;你要是听到脏话,我可能会怀疑他们要离婚了。当同学的爸爸和我们一起踢球、撞身体、倒地上骂人,我会有点羡慕他们那种很亲切的人性,像一个可以兼职做你的朋友的爸爸。我爸对我始终会保持善良礼貌,偶尔有点小幽默,偶尔有点客气。他明明有所有“好父亲”的分儿,但是总觉得缺点什么(可能对于“好父亲”的标准就是缺乏和子女达到充沛的情感链接这个指标)。我那么期待听他大声骂一句脏话,也许是因为很想知道自己也可以,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我有一个发泄情绪的窗口。居然是足球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
在我们家里的地下室,借助卡罗足足的火气,我和我爸不约而同地加入了。我爸会从比较纯洁的词儿开始,花一些文学性的心思来形容粗暴地犯规的对手(“铁匠!屠夫!”),再跟着氛围的紧张程度上升放过自己的想象力,来点更直接的。心情激动时,卡罗的脸会发红——我妈不太会下楼,但是看到卡罗离开我们家时不止一次为他的冠状动脉担心。我和卡罗会拥抱,摇晃对方的身体,非常的减压。2003年,AC米兰拿欧洲冠军的那天晚上,舍甫琴科的最终点球进了之后,卡罗直接跳到地下室的沙发床上,把我彻底压在他身体的下面。我和我爸不太会有肢体接触,但是仅仅一起经历一个可以随意表达的空间,对于丰富我们关系的情感纬度也足够了。
自从我离开意大利搬到中国,尽管我们的距离遥远,我爸会很细致地关注我最近的生活动态——他会知道我的签证到什么时候,我在拍什么片子,我要交什么稿。他会将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文字和图片、还有我们在家庭群的聊天记录全部收藏,过了段时间把这些混杂的内容排版整理成一个概括我的某个人生阶段或生活经历的PDF文档(类似于苹果手机自动生成的回忆时光视频)。我关于他的生活的信息就没有那么多了,只靠每月一次左右的视频电话来简单了解一下。2020岁末,我记得看到了一条新闻,八十年代的意大利球星保罗·罗西因肺癌去世了。我当时就惊讶,这不是我爸年轻时会看的球员吗?查了下,保罗·罗西确实是1956年生的人,比我爸还小三岁。我感到全身一阵颤抖。
我在异国他乡经历着期限不明的疫情,而我爸,他还能有多久呢?在那不久后,我还收到了消息,我爸在公司得了新冠,更是觉得完蛋了。后来他迅速康复了,又开始了走路去上班的日子,我稍微放心了。但是我承认,这次回家有一种和他每次相处都很宝贵的感觉,虽然我试图不让对方察觉到,免得气氛过于沉重。能一起看球赛,自然也是我很珍惜的活动。
最近一个周六晚上,我坐在温州餐吧的椅子上,点了一个啤酒。比赛已经踢到了一半,卡罗才到:“我找停车位置找了二十二分钟。”他张开双臂来表示无语,通知餐吧的所有人,接着脱下羽绒服和围巾,找个椅子坐下来。
“你爸呢?”卡罗问我。
“他今天去了公司,应该马上能来。”
“周六去公司了?”
“为了上一个网课,他觉得去公司比较能专心。”
卡罗的好奇心差不多耗尽了,他想看球赛,而不是仔细了解为什么一个七十多岁、名义上已退休的老人还要在周末去公司接受在职进修教育。
比赛很顺利,AC米兰主场对阵恩波利,莫拉塔进一个,赖因德斯进了两个,轻轻松松的三比零。使我不安的,反而是我爸的缺席。他在比赛开始一分钟前给我发了消息,说他还在听网课,下半场再到餐吧。我一直帮他留了位置,放在我前面的一把空椅子,每次有人上厕所时就会成为某种物理障碍——这样干扰别人的行动,还占领一个很好的位置,我感觉挺不好意思。我时不时往左边望着,看有没有人从餐吧的门进来。比赛都结束了,我爸也没有发消息。我们本来打算看完比赛,等我妈来接我们一起去吃希腊菜。结果,我到温州餐吧的对面找到我妈时,她说我爸决定不去了,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们也回去。
听我爸抱怨网课的系统(课程中设置了突击测试,回答错了要从头开始,所以他费了比预期更多的时间),远没有和他一起骂裁判有趣。甚至,我发现一起看球是我们关系中很重要的调节器。第二天,终于闲了,我爸和我搭起了话。“你有没有考虑过找媒体报道你?”我爸问了。“这样出版社应该会排队来找你签约。”
我最近确实想在意大利出书,在和不同的出版社联络。但是,那样的主意——到底是什么主意?被媒体报道会更有可能找到出版社,我不知道吗?是我不想吗?说都说了,你是那边有办法吗?我有点怒了,又无处表达,只能避开对视摇摇头,温和地反驳这个起不到作用的建议。说到底,我家里没有写作的,也没有做文化行业的,大家确实帮不上我什么忙,可是又如此执着于为我指路,这还真是挺无奈的事情。
当然,这也是源于笨拙的爱的举动——想要帮助,无论这有多么地不可能。对方的意图如此之善,我的反感注定会被理解为我的难缠。怎么说呢,一旦真的和我爸朝夕相处,我们沟通上的困难会露出:我的事业成为了我们之间被默认的共同话题,只要他找我闲聊,不是和我汇报我的书在豆瓣条目最新的数据,就是问我找意大利的出版公司有没有消息。这些话题确实能够拉近我们的距离,但又对我并不轻松,反而会让我觉得压力更大,有时一说起来就感觉吃不下饭了。一周下来,星期六去温州餐吧看赖因德斯进两个球,听卡罗坚定地否定AC米兰教练所有的选择,还是挺有必要的。
在足球上,我不见得总是和我爸达成共识:他无可避免地依靠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足球来说事情,因此会提出多少有些过时的观点(他觉得AC米兰的防守问题需要通过增加一个没有盯防义务的中卫去解决,虽然这个踢法已被放弃三十多年了)。聊到频繁的球员转会时,必然会听到我爸回忆起他小时候的偶像路易吉·里瓦——他是如何拒绝签约尤文、坚持留在小球队卡利亚里充满感情的故事。我每次听了都会假装是第一次。我凭什么要让他意识到,让他不再提起一生一次年轻时看球的经历?在中国,我认识了不少70后和80后的AC米兰球迷,他们年轻时赶上了荷兰三剑客的黄金时代,至今记得小时候在CCTV看意甲传播的时光。我和几个比我大些的意大利朋友有个闲聊的微信群,里面经常聊足球,但几乎都是关于2000年以前的话题了。我呢,二十年后仍然绕不开舍甫琴科的那次拿下欧冠的点球。在足球上,我们各说各的,又能如此坐在一起,九十分钟又九十分钟。
圣诞节前几天,我们在家里和卡罗一起聚了一下。这次,他的老婆也在——算是两个家的相约,为数不多的、不围绕着足球和卡罗的社交。听他讲关于体育之外的话题,我有点不习惯了,以至于无法当真。卡罗说我“适应能力极强”时,我听着就像是在夸一个在意大利北方顺利度过了冬天的巴西后卫。当我们准备告别,卡罗提起一个我应该是努力避开去想的问题:因为圣诞假期过后我就要离开了,我们不会有机会一起看球赛了。我对卡罗说应该还来得及看一场,但等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他说得对。这个现实和AC米兰今年的表现一样令人心寒。我,我爸,卡罗,一场欧冠,也许我真的想念这些在电视前的夜晚。这次回意大利,我还是很庆幸我们找回来了作为三个球迷的相处。等下个赛季,我们温州餐吧见吧。
本文编辑:刘水(@Sally博物馆)、天使望故乡
这是一篇免费文章。如果你喜欢并希望支持我以后写更多的内容,请考虑成为随笔ale专栏的会员!
我也不懂是怎么陷入的职业性地狱
在意大利读本科的时候,到罗马租房子,我会为了和美国室友有共同话题而追他追的剧——我们在厨房或客厅相处的时光,产生了大量不痛不痒的话题的需求。我尝试拉近距离聊彼此的生活时,问他具体做什么工作,他都......
九年一次的圣诞节
上次参加我妈妈那边亲戚的圣诞聚会,是2015年。这是自从我记事起就有的传统:在我妈妈表妹家那里举办,来的一般有三十多号人,都是和她或多或少有血缘关系的人,像我舅舅,但是也有一些我至今搞不太懂是谁......
钱的善意
“你知道,这个城市还是挺贵的,你如果不是靠家里的企业,这还是一份能让你在这里生活的工作。”
握着一杯内格罗尼说着这句话,我的放射科医生朋友带着一定的阴阳怪气描述自己的职业。在今天晚上......
专栏的圣诞小聚(北京+欧美时区两场)
hi!
圣诞来临,也很久没有见到大家,很想邀请专栏的所有读者到线上聊一聊~欢迎本周日12月22日参加专栏的圣诞party!
来了的人有机会拿下一年的专栏订阅礼物(现场抽奖......
说破无毒:鼓起勇气,写点意大利语
我在这方面的失败是有可见的痕迹:2024年2月4日,我开启了一个newsletter,准备用来定期发表我的非中文写作。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在主要用中文写作的三四年之后,重新恢复和不讲中文的世界的......

